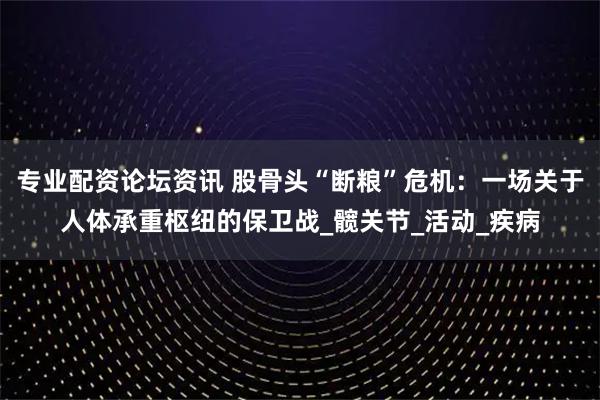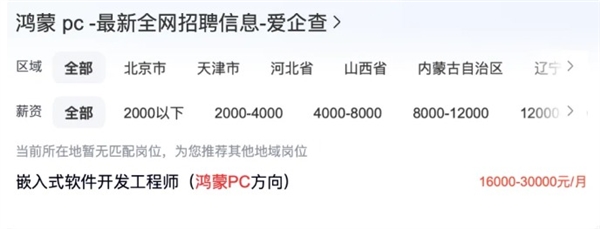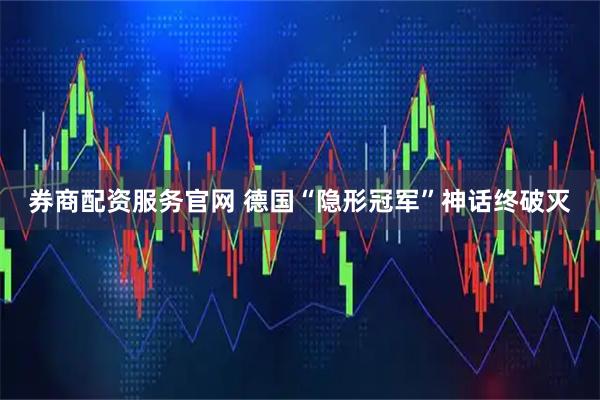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李士运的杭州工作室,画架上未完成的布面油画沾着新鲜油彩配资入门知识网,大片留白托着一枝孤挺的玉兰,油彩稀薄如宣纸上的水墨,边缘洇出不可控的淡青痕迹。空气中弥漫着松节油与旧木头混合的气息,渠梁坐在藤椅上,看着这位总在画布上做东西方实验的艺术家,抛出了关于文化输出的疑问。
一、您觉得现在中国文化成功输出的关键是什么?
李士运正用西洋画刀调整画面肌理,闻言抬了抬眉,蘸取颜料的手停在半空:“得先想明白,我们的根在哪里。我的东西从一开始就锚定中国的、东方的根基,但拿出来得能在国际舞台上和西方文化对话,不是自说自话。”他指着墙上一幅画,画面里是水墨意境的山峦,却用油画颜料堆出了厚重的质感,“就像这个,内核是东方的情调,但语言得让别人能看懂。”
二、当矿物颜料遇见“计白当黑”:技法里的文化对话
工作室的创作台堆满中式颜料碟,工具却是西洋画刀。李士运摒弃油画惯用的厚涂法,转而让油彩在画布上流动、渗透,模仿水墨的氤氲感。《黛瓦修竹》中,黛色屋檐线条刚硬如刀刻,竹叶却以没骨技法晕染,留白处如雾气弥漫。“中国画讲‘无画处皆成妙境’,油画留白是冒险——稍有不慎就显空洞。”他指着画面中央一道飞白,“这一笔是偶然,也是十年功力的必然。”
展开剩余70%这种探索曾被质疑“不伦不类”。2015年《粉园》参展时,有评论家直言:“油画追求形质精准,何必附庸风雅?”李士运的回应藏在实践里:他将文人画题材植入油布,却用西方点线面解构。《花期时时》系列中,传统工笔花卉旁排列着数码圆点矩阵,如同当代版题跋。“圆点是向蒙德里安致敬,但排布方式参考了《芥子园画谱》的章法。”在他看来,冲突感恰是对话的起点。
三、从常玉到哪吒:共识如何诞生?
聊到近年出圈的文化产品,渠梁提起《哪吒》的成功。李士运放下画笔,语气认真起来:“哪吒为什么能成?它给那个大IP注入了当代人能共鸣的精神内核。我有很深的东方文化情结,哪吒是东方的,但创作它的技术得是国际的。你试试用水墨的方法画哪吒的画面,未必能打动那么多年轻观众,更别说走出国门了。”
话题转到艺术家常玉,李士运的眼神柔和了些。他泡开一壶龙井,谈起常玉在巴黎的旧事——野兽派色彩包裹东方写意,一朵孤菊拍出十亿台币。“现在大家都在说常玉,他的画确实值得琢磨。台湾画廊包装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那个平衡点——用老外熟悉的造型方式、色彩逻辑,装进去东方的内容和情调。”他走到一幅临摹常玉风格的小品前,“他构建了一种共识,让西方观众能透过他们熟悉的艺术语言,感受到东方的韵味。”
在李士运看来,常玉与哪吒有着共通的智慧:“常玉以马蒂斯的色彩画菊花,哪吒以好莱坞叙事承载道家哲学。所有成功输出,都在回答一个问题:如何让黄河之水流入塞纳河,却不改其浊?”
四、俗与雅的边界:让传统带着体温呼吸
谈及“中国审美是否在慢性自杀”的争议,李士运沉默片刻,随后指向工作室墙角立着的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海报:“与其说自杀,不如说有时候太端着了。有人觉得艺术就得高冷,但你看那些能流传开的,多少都带点‘俗’气——不是低俗,是贴近生活的烟火气。”
这种对“俗”的思考,化作他创作中更隐秘的尝试。2023年杭州《無界之界》双个展上,《西湖紫藤》引发热议:紫藤以写意泼彩呈现,背景却用几何色块分割空间。一位年轻观众在展签留言:“像把西湖装进赛博屏风。”李士运说:“所谓‘俗’,是生硬贴文化标签;真正的东方性,藏在观察世界的视角里——就像哪吒用3D技术打斗,内核仍是‘我命由我不由天’的反骨。”
工作室的光线渐渐暗下来,李士运拧亮台灯,灯光在画布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他近期的新作《山外》立在画架旁,两米高的画布将山水抽象为色层碰撞,留白处拓印着宋代山水画残片。“我在想,如果常玉活在今天,会如何用AI重构‘留白’?”他笑称自己正在“危险的实验”——把倪瓒的枯淡变成油彩的极简,让黄宾虹的“墨团团”对接蒙德里安的方格子。“有人说这是慢性自杀,但传统若不能与当代共生,才是真正的消亡。”
雨停时,画布上的玉兰已添新蕊。李士运最后盖上一枚朱文印章:“印是传统符号配资入门知识网,但印文是‘0与1’——这是我的时代注脚。”玻璃窗外,西湖雾气升腾,仿佛他画中未干的留白,正等待世界落笔。
发布于:浙江省天牛宝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